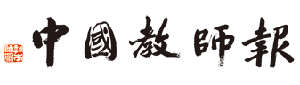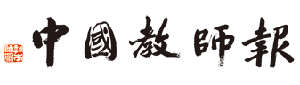作为国际知名的科学家、教育家,79岁高龄的台湾“清华大学”原校长刘炯朗退休之后,一直致力于打通科学与人文的联系,涉猎写作、翻译、广播等领域,深受民众的喜爱和推崇。近日,刘炯朗抵京进行新书宣传,并到北京四中等学校进行演讲。宣讲间隙,本报记者就教育相关问题专访了刘炯朗。
考试制度训练出来的学生,目光短浅
中国教师报:谈到中小学教育,学生负担过重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对于中小学学生沉重的学业负担,您是怎么看的?
刘炯朗:在目前的环境下,内地和台湾的中小学生考试压力都是非常大的。考试的压力让我们的学生在中小学阶段没有发现学习的快乐,没有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正确的学习态度。所以谈及今天的教育,我们常常会觉得它无法培养出很多的世界级大师,因为我们的学生没有创新能力,没有领导能力,没有幽默感,没有优秀的口才。起码在今天的内地和台湾,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目光很短浅,视野很狭窄。如果我们一直不能从考试的囹圄中跳出来,势必会影响未来的人才培养。
中小学是教育最重要的一个阶段,我们的教育要以这个阶段为基础,培养真正的读书人,培养社会真正需要的人才。
中国教师报:刚才您谈到中小学是教育最重要的一个阶段,在您的心目中,教育分为哪些阶段?
刘炯朗:我做一个非常简单的回答,我把教育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幼儿园阶段。
幼儿园是很多小朋友第一次有机会离开家,跟他不认识的小朋友学习怎样与他人一起学习和游戏,仅此而已。
第二个阶段是小学和初中阶段。在这一阶段,我们要培养孩子读书的习惯、读书的态度,引导他们发现读书的乐趣,而不是一味强调书的内容。但在今天的考试制度下,孩子并没有养成读书的习惯,只是养成了考试的习惯;他们没有养成良好的读书态度,而只知道准备考试的态度;他们没有发现读书的快乐,只知道补习的痛苦……
我始终认为,小学和初中阶段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一个真正做学问的人的许多素养都是在该阶段培养出来的。
第三个阶段是高中和大学的7年。在这个阶段,学生的心智已经趋于成熟,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做好踏入社会或者从事更高深的学问的准备。
中国教师报:在现有的环境下,要培养真正做学问的人,中小学教育需要怎样改变?
刘炯朗:我们不要谈怎样改变中小学教育,这是个复杂的问题。学生在第二阶段缺失的教育,我们可以在他们进入大学之后帮他们补回来,即实施恰当的、要求严格的、有趣味的通识教育。实施通识教育需要我们下大决心,因为只有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让学生享受真正的通识教育,让学生通过大学4年的学习后,成为名符其实的读书人。
在通识教育中,寻到知识相通的乐趣
中国教师报:您所理解的通识教育是怎样的?
刘炯朗:举一个例子,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他们看重的通识教育主要包括以下5个方面。第一也是最重要的就是道德修养。第二,独立思考的能力。第三,善于表达的能力。第四,聆听的能力。第五,了解、接受世界的多元,并能体会多元之美。但是,实施良好的通识教育必须建立在对某一门学科深入了解的基础上。对专业的深入了解,目的并不是把学生变成一个进入企业就能做工程师的人,它的目的是经过对学问的深入探讨,让学生知道做学问的态度应该是怎样的,做学问的困难有哪些,做学问有哪些快乐。
中国教师报:怎样做学问才能获得快乐?
刘炯朗:关于这点,我想讲讲做学问的功夫。我大学读的是电机工程,后来到美国读的也是电机工程和电脑科学,从事的也是这方面的研究。我学习的底子是小时候学中文打好的,很多小时候背的古诗词我现在还记得。
我想说的是,学问是相通的,只要有一点线索,然后跟着去寻找,便会发现更多的知识,无穷无尽。诗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里面有很多脉络、很多知识,看似凌乱,但当你的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可以将它们连成一套知识。
举个例子,有一副对联很有名:“天若有情天亦老,月如无恨月常圆”。“天若有情天亦老”是个非常好的上联,出来以后等了两百年,到了北宋,石曼卿才把下联对出来。我读这个对联时的第一反应是觉得石曼卿的灵感一定来自苏东坡的“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可真的是这样吗?到底是石曼卿启发了苏东坡,还是苏东坡启发了石曼卿?于是,我仔细查阅才发现,石曼卿比苏东坡早出生50年,这个线索或许可以说明苏东坡的灵感来自石曼卿。
我做了40年半导体科学的研究,但学问和知识是相通的,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相互之间有合理解释,让我找到这个解释,这就是学问的乐趣。我认为学问做得好的人,在8个方面会很突出:敏锐的触角、广泛的兴趣、深入的探讨、丰富的联想、严谨的判别、开放的思想、苛求的完美,谦卑的努力。
中国教师报:您一直强调通识教育,那么,在怎样的通识教育之下,才能让人们找到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相通的乐趣?
刘炯朗:8年前,我开始在台湾主持一个广播节目《我爱谈天你爱笑》。当时他们找我的时候出于这样的考虑:新竹是个科学园区,我们能不能有个电台既讲科学,也讲人文、艺术,把看上去互不相关的事物间的内在联系找出来。语言之间也有关系,小孩子学很多种语言,中文和英文之间有关联,往往母语学得好,第二语言才会学好。因为发音、文法是最表面的东西,内在的是你的理念和思想,内在的层面是完全不一样的。语言最重要的是情感和理念的表达,中文好英文就会好,但现在我们教育很大的一个问题是学生写作文的机会太少,只背若干篇作文,然后就用同一模式对应不同题目,完全没有根据学生的思路进行训练。我是教自然科学的,经常发现学生写报告的思路不对。
今天,我们讲通识教育,假如我能够定义通识教育的话,我会要求学生上非常好的国文课,非常好的英文课,我也希望学生能够上非常好的电脑课,有关统计的课,等等。通识教育不应该分专业,任何东西,只要是有趣的,在学术上有吸引力的都要做,但是必须好好地做、非常努力地去做。通识教育是人一生的事情,不是大学时才要做的,是一个人一生都要坚持的事情。
为学要如金字塔,又能广大又能高
中国教师报:作为一位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您可以说已经功成名就了,那么,现在您学习的乐趣又来自哪里?
刘炯朗:我一周讲20分钟的《我爱谈天你爱笑》,有人说我这是放下身段,面向大众讲通俗的知识,但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现在做的事,完全是为自己能在学习中得到乐趣,是为自己做的。每周准备广播的内容,思路并不是一开始就知道的,常常是周二才有灵感知道这周讲什么,用两天准备材料,用一天写出一篇3000字左右的文章。我上个礼拜讲了5首《满江红》,岳飞写的一首、辛弃疾写的3首,同样的词牌可以写不同的感情,这些词很多都是我小时候背下的,少时学到的东西,一辈子受用不尽。
现在,理工学科和人文学科界限分明,《我爱谈天你爱笑》就是我的读书笔记。我从小受到很好的训练就是给我一个读书的态度和读书的乐趣。一个人成功靠两样东西,一靠努力,二靠运气。
中国教师报:对于现在的年轻人如何做学问,您有什么建议?
刘炯朗:所有人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都会讲3个字“多读书”。现在有许多人认为书太多了,不一定所读的书都好,不一定要读书。这是一个漂亮的借口,但你会因为食物太多而放弃享受美食吗?面对现在的年轻人,我总跟他们说,上学的时候一定要多读书,广泛而快乐地读书,你现在读的东西一辈子都不会忘。
我是想通过自己的一点努力,让年轻人知道,知识是相通的,学工科的人,也需要懂诗词,也要懂历史、哲学,这些对你做学问是有极大裨益的。但这些知识的获得是要趁早,我现在记得的所有诗词都是我16岁以前背诵的东西。现在信息这么丰富,“一次看懂自然科学”、“一次看懂社会科学”是不可能的,而是一生都要做的。
另外,现在好像大家都觉得,通识教育讲得很多,通识教育是不是抢了专业教育的时间,占了专业教育的地盘。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专业能力不够,将来会不会没办法做事情,没有饭吃。对于这点,我完全不同意,首先,通识教育是教育里特别是大学教育最重要的一环。其次,通识教育跟专业教育是相辅相成的,通识教育不占专业教育的地盘,专业教育也不会占通识教育的地盘。
胡适先生说过两句话,为学要如金字塔,又能广大又能高。其实后面还有一句:才能历久不朽。
当校长不能靠威权,要让大家信服和敬佩
中国教师报:现在内地提倡教育家办学,可以说校长是离教育家最近的一个群体,您曾经当过台湾“清华大学”的校长,在台湾,校长都有哪些权力?
刘炯朗:这个很难回答,我不知道怎么样给权力下定义,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教育家、读书人,某种程度上是由自己的付出决定的。尤其是在学校里,我认为校长不可能有威权,校长应该有说服众人的能力,但是同时,校长要有影响别人的能力。假如校长只靠说服的话,很多事情是不能决定的,校长必须要有最后下决心的能力。但是校长,特别是在一个大学,或者一个教育机构,靠威权来下决定是下不了的,校长必须靠两个事情来下决定。
第一,他的决定是否得到大家的信服。第二,他的人格是否受到大家的敬佩。校长下的决定,第一要有他的道理,有他的用心。第二,虽然我不同意他的决定,但是我敬佩他的人格,所以我可以接受。威权不是任何人可以给你的,特别是在一个教育单位,威权是你赚来的,威权是你营造出来的,那样的威权才是真正的威权。
中国教师报:在您的心里,我们的教育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刘炯朗:关于这个问题,我记得希腊有位教育家曾经讲过,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一个有学问、有道德、有用的人。我觉得讲得很好,虽然听起来很虚,但仔细分析一下,这就是教育最重要的目的——培养三者并重的人才。问题是,在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大学教育都认为“有用”是最重要的目标,甚至是唯一的目标。而不知学问与品格同样重要,而且有学问、有品格与有用并不违背。
学生只要能读完大学,做一个有品格的人,毕业后都能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不用像我小时候那样,为吃饱饭而担心。在当今社会的大背景下,不读书的学生反而会面临更大的考验。
这就是我们心目中所谓的完整的教育,既包含了通识教育,又包括了专业教育,这个并不是互相抵触的。我们要把教育看成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学校如同一个有温度的“热水瓶”,我们的教育就是让学生在“热水瓶”里成长,在这个“热水瓶”里面,我们跟所有的学生和教师互动,从而成为一个快乐的人。
刘炯朗,广东省中山县人,台湾著名教育家、科学家。曾任教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伊利诺伊大学,于1998年出任台湾“清华大学”校长,2000年当选台湾“中研院”院士,2002年从“清华大学”退休。2005年,他开始主持电台节目《我爱谈天你爱笑》,每星期主讲20分钟,话题涉及工、理、文、史、哲等领域。他日前在内地出版的新书《一次读懂自然科学》、《一次读懂社会科学》曾被马英九推荐为2011年台湾暑期青年阅读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