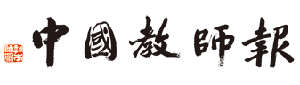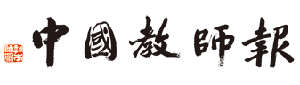小河无水大河干,当所有的“微环境”都呈现良好的态势,何愁整个教育生态不健康?从学校的课堂生态到师生的成长生态,再到学校的文化生态,作为教育管理者,应该如何有效引领、科学营建适宜各种“生物”生长的良好生态,让每一所学校都成为一片丰饶的“花园”或“池塘”?本期,周刊特别关注学校“生态学”,为您解析区域整体改革发展大形势下,构建和谐学校生态的意义与方法。
一个面积只有七八亩大的袖珍学校里,有沙池、梅花桩、攀爬墙、古诗墙、生态园、美术角等24道人文景观,它们共同构成了学生喜欢的“生态校园”。这是很多到访过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西下池小学的教育人对该校的认识。
有一所中学,全体教师的平均年龄不到30岁,他们每天穿梭于各个教室,常常隐没在学生中,与学生一起在课堂里成长;学生真正主宰了学习,自主成为他们成长的最佳选择;不管是教育同行还是学生家长,都在敞开的校门里受教,开放成为学校发展的最好心态……这是湖南省株洲市景弘中学令人羡慕的师生发展生态。
在北京的一所高中,学校开设了265门学科课程、30门综合实践课程、75门职业考察课程,272个社团和60个学生管理岗位,为学生成长提供了多样化选择。学校全面实施分级分类课程、走班选课,4000多名学生,每人一张课程表,真正实现了课程超市自主选择的成长生态。
……
这些典型学校,无论是在学校文化、师生成长方面,还是在课程建设、课堂教学层面,都共同指向一个美好的词——生态。
生态,通常指一个特定区域内各种生物的生存与发展状态;一个理想的生态环境,必将以多元共生的生命价值观为底色,通过接纳、包容和调和,组构一个具有自我调节能力,有利于各种生命体成长的动态环境。人们常常用生态来定义许多美好的事物,教育亦不能外。那么,对于学校来说,到底需要怎样的生态?除了校园环境外,学校应当如何营建教育生态?
学校是一个文化生态系统
“当我们以生态学的观点审视教育,并以此为基点追问学校育人目标时,会惊讶地发现,我们通常所说的学校发展水平,本质上就是学校教育生态的构建水平。”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教育局副局长陈国安如此看待教育生态。
早在上世纪70年代,国外教育生态研究方兴未艾。美国教育史学家劳伦斯·克雷明曾说,研究教育生态学的方法就是“把各种教育机构与结构置于彼此联系中,以及与维持它们并受它们影响的更广泛的社会之间的联系中来加以审视”。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教育生态学的研究范围才得以拓宽和纵深发展,更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学校生态学,美国华盛顿大学学者古德莱德首次提出:“学校是一个文化生态系统。”
“学校生态环境不是孤立的,而是区域生态群落中的一员。”四川省泸县教育局教研员梅永轩指出,区域教育生态与学校生态总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因此,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教育人,将目光聚焦在学校教育生态的三大核心要素——人、环境、资源,并以“人”这一不可替代的生态核心为基点,全力推动三者之间有效联系、彼此作用,逐渐向“享受教育”的理念靠近。在河南省安阳市殷都区,区委、区政府领导高度重视,构建学习型系统,创立“三主体”论,建立实行考试、考评、考核相结合的学生“三考”评价体系,不仅有力地保障了区域课改的有效推进,更为学校和师生发展创设了自主宽松的环境。
广东省深圳市清林小学,取消了“三好学生”的评选,肯定学生好的方面,发现每个孩子的长处。该校校长杨勇认为,“教育首先是一种欣赏,因为教师的眼光将决定孩子的一生。”
在西下池小学,学生如果不想听,就可以不上课;如果不想写作业,也可以不写。那些选择不上课的学生,一般都会在不影响别人学习的前提下,找自己感兴趣的事做。比如,他们可以去沙池里玩个大汗淋漓。对于教师,西下池小学校长李艳丽会帮助每位教师建立对工作的责任心,然后让每位教师制定个人成长规划,这个成长规划中会有她推介的一个阅读书单。
如果说,指向人的可持续发展这一核心的学校教育文化,更具生态性的话,在国外,一些彰显人文关怀的教育案例,也值得关注。新加坡的学校大多采用中空结构,不仅为学生穿行提供了方便,更大大地拓展了学生的活动空间。校园里,随处可见席地而坐的学生……一位生活在美国的父亲,分享孩子在美国做家庭作业的经历时说,有一天孩子拿回家一个盒子,里面的纸条上写着:“请找到我们需要的这些东西,不允许花钱买!”接下来列了一系列物品,包括一张早已不存在的国家地图,一个死掉的细胞,等等,还有一个最简单,却也最有意思的问题:计算学校10位教师的平均年龄……
北京市教委委员李奕曾撰文指出,一所学校就是一个小的生态系统,是否和谐,校长的办学思想和教育理念至关重要。在营造学校生态的过程中,教育者的价值观能得到充分体现,而一个地区基础教育的和谐、繁荣,有赖于区域内每一所学校能得到适合本校的发展空间,实现个性发展。
教育生态的落脚点在课堂
“生态课堂是学校教育生态的落脚点。鼓励、引导教师用新思维、新思想重新构筑生态课堂,构建师生自然、和谐的关系。”拥有多年教育教学经历的山东省临邑县第二中学教师刘洪华,将构建学校生态的落脚点引向课堂。当下诸多课改学校正是通过课堂突破,实现了学校生态文化的重新建构。
河北省围场天卉中学在创新“大单元教学模式”之后,又吸纳两大教学研究成果——高效阅读和高效写作,将其扩充为“大展示、大单元、大读写”新高效课堂模式,即“3D新高效课堂”。该校学生被这样的课堂所吸引,“过去怕上课,现在我怕下课。在这种课堂里,不但学到了知识,还锻炼了胆识和表达能力,现在即使放假一天,我都想立刻回学校。”一个学生如是说。
当构建学校生态落脚在课堂,“在各种学习活动中,师生将共同创设能够实现共同成长的教育环境。”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黄龙新桥小学教师陈海军,一直用行动诠释生态课堂。在其邻省安徽,铜陵市铜都双语学校的“跨界大课堂”每天都是新的。他们根据同年级学生的个性、学业水平等情况,组建“学生发展共同体”,共同体在“文化空间站”里学习。在那里,“班级”是流动的,教师是走班的,学科是综合的。在景弘中学的“自驾”课上,教室里没有一位教师,但学生依旧有秩序地学习、展示、评价。有时,教师或同时给两个班上课,或多位教师在一间教室聚集,直接参与讨论,并在学生展示时提出疑问、作出点评。
上海市平和双语学校副校长王玮,2012年曾到美国波士顿学习、考察。在一节跨学科教学的合作课上,英语和历史教师共同完成教学工作。两位异国教师的举动,让王玮意识到教师协作完成教学工作,“对教师与学生来讲,都是更自由、更易接受的教学方式”。
自由是生态课堂的重要特质,体现了尊重与信任。曾有媒体报道中国教师朱琴琴到英国一所社区中学学习的故事。当朱琴琴看到学生在课堂的状态,她很吃惊:一些学生在教室后面翻书、玩游戏,一些学生在讨论计算题,还有一些学生在接受教师辅导。尽管教学秩序不整齐,但课堂气氛却很活跃、热闹。据这所社区学校副校长介绍,英国没有统一的教科书,教师都是参考教育书籍和学生的接受能力,自编教学计划进行教学。课堂上的主要任务是提纲挈领地讲透教材的主要内容,然后进行巡回解答和指导,整个教学过程是教师围着学生转。“你告诉我的,我会忘记;你给我看的,我可能记不住;你让我加入,我会永远理解。”社区学校校长如是说。
但在现实中,并不是每一所学校都会给学生自由的空间,朱琴琴反思道:“我们更多的是让学生听话,做乖巧的小绵羊,可这样压抑了孩子顽皮的天性、想象力和创造力。”
不同的课堂生态,成就了不同状态的学生。“我们有时候羡慕欧美国家的学生创造力强、自由洒脱。有时候羡慕日本学生纪律性强、整齐划一。我们的问题,不是没有关注到学生‘收和放’的问题,而是如何明确‘收和放’的尺度问题。”江苏省南京市下关区教育局副局长周斌,在赴日教育考察笔记中这样写道,“教育的尺度如果本身摇摆不定,‘放’的方向上,没有能够明确培养目标,‘收’的尺度上,没有能够明确常态活动中的禁区和高压线,具体的教育措施就无法得到实质保障。”而“收和放”的尺度,在不同程度上决定着课堂生态的形成。
学校呼唤“绿色”评价
不管在人类社会,还是在教育领域,学校评价都是绕不过去的话题。一方区域的教育生态,既取决于区域内各学校的小生态系统,也受制于区域整体评价系统的构建。
在芬兰,学校间从不会有竞赛、排名。芬兰法律规定,学生在6年级之前,学校不能以等级或分数来评断他们。所以人们常常看到,6年级的芬兰女学生就开始化淡妆或挑染头发,但师长却任其发展,从不刻意禁止、管制,这反而使学生变得落落大方、成熟自然。
芬兰教育的另一可贵之处,就是尽可能地不比较、不评分,无论是对学生还是教师。学校不对教师进行评比,也不考核、督察。但是,每隔一段时间,教师会收到不同意见与满意度数据,让教师对学校、家长、学生等各方信息有全面的了解,进而促其反思和改进教学方法。芬兰拉普兰大学教育系附属实验学校校长瓦菈能博士曾表示,“我不需要去管教师,教师的教学如有问题,最后一定都会反映到我这里来。如果我去管,表面功夫谁不会做呢?你要什么数据,人家就给什么。你一来,人家就做个标准模样给你看。可是那有意义吗?对学生有益处吗?对整体教育发展有帮助吗?”
学校、教师之所以会用如此轻松的心态面对繁重的教学工作,是因为芬兰主管教育的行政机关,从不做起跑点不公平的评鉴,而给予校长、教师、学生同等的学习、成长机会与动力养成,让他们依照全国教育核心课程纲要,自行订立自己的教学目标与希望达成的效果。
在邻国日本,学校每年只需进行一次自我评价,评价的内容由学校自行确定。评价的结果报都道府县教育委员会,便于各教育委员会对学校工作的监督。在日本的一些地方,社会机构或家长也可以要求学校公布自我评价结果。因此,日本的学校评估不仅由教育评估部门进行,还会广泛吸纳社会参与,如向家长发放问卷、召开社区座谈会等,力求使评估结果更加客观、公正,同时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支持教育。
而今,我国很多地区教育行政部门也认识到这一问题,并积极行动,改变传统的学校评价标准,如上海市出台《上海市中小学生学业质量绿色指标(试行)》。上海市奉贤区五四学校教师唐冰,认真对照了新旧指标后认为,“绿色指标”体系的内涵更广阔、构成更合理、衡量更科学。教育评价,从结果性评价向过程性评价转型。对学生的评价,逐步发挥综合素养评价手册的作用,加强对学生的学习过程进行记录和评估;对学科教学的评价,重视专题调研、听评课制度的建设,关注常态下教学质量的提升;对学校的办学质量,通过发展性教育督导的方式,帮助学校分析发展规划、明确发展的重点,并对影响学校发展的关键问题予以支持和点拨。让评价成为促进学生、教师、学校发展的源动力。
与此同时,上海教育行政部门也积极推动政府职能从管理向服务转型。上海以管、办、评分离机制建设为重点,形成了“政府宏观管理、学校自主办学、中介优质服务”的教育发展新格局。学校积极探索章程统领下的现代学校制度建设,同时采用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将薄弱学校的托底工作、教育评价等一系列专业工作,交由相关的机构实施。教育行政的转型,激活了学校的办学活力和专业机构参与教育事业的积极性,构建了教育发展的新格局,使得学校发展更“绿色”。
北京市教委主任线联平也曾指出,促进每一个学生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既是提升学校教育质量的核心任务,也是开展学校教育质量督导评价的主要目的,应当据此制定学校教育质量的督导评价指标体系,督促和引导学校的教育工作聚焦于学生的健康成长,服务于学生的全面发展。
(下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