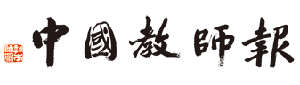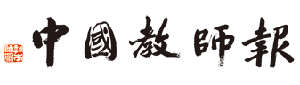1946年,随着西南联合大学办学结束,1942级历史系学生胡邦定告别学习、生活了4年多的母校。如今,近70年过去了,但半个多世纪的风霜雨雪,并没有磨灭胡邦定对母校的眷恋,当年那些令人高山仰止、灿烂了中国教育历史星空的大师们,依旧鲜活地留存在他的记忆中。每每念及恩师,胡邦定总会脱口而出8个字:学为人师,行为世范。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记者采访已经93岁高龄的胡邦定,听老人讲述大师风范以及恩师给他的教育。
大师如云
“名师荟萃,群星璀璨”,这是胡邦定对当年西南联大授课教师的第一印象。据他回忆,大一新生的课程基本都是必修课,包括国文、英文、中国通史、逻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伦理学等,均由名家授课。教国文的有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等;担任过英文讲席的有叶公超、钱钟书、卞之琳、查良铮等;而教逻辑学的是名教授金岳霖;教伦理学的是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教经济学的是法商学院院长陈岱孙;教政治学概论的是著名政治学家张奚若、浦薛凤、楼邦彦等大师;教社会学原理的先后有陈序经、吴泽霖……无论哪门学科的教师,皆为学贯中西、博通古今的大家。
但是,并不是每个学生都能有机会听到大师的课。“比如,西南联大的大一国文课有许多名师任教,而且都是小班,一班不过二三十人。谁分到哪位教师的名下,并不是由学生自选,而是由教务处分配。”胡邦定回忆说,如果当时让学生自己选教师,恐怕朱自清、闻一多等授课的班就会爆棚,而个别学问虽深、但讲课不一定精彩的教师会“门前冷落”。
严格要求
胡邦定很幸运,大一时遇到了著名历史学家吴晗。当时吴晗很年轻,1942年时不过33岁,风华正茂,讲课也颇多创新:一般传统历史教学按朝代顺序讲,但他讲课是按石器时代、殷商社会、春秋封建、战国七雄、土地制度、从募兵到征兵、刑法制度、科举制度等专题来讲。“这给我一个启发,对史料要进行综合分析,要多读书;掌握丰富的资料,从中形成自己的观点。泥古不化是不可能有创意、有发展的。”直到现在,胡邦定仍然感激吴晗对自己的史学训练,但当时学生们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吴晗的严格要求,“我们这一班学年结束考试的成绩,最低的只得12分,还有59分的,我考了第一名,也不过76分。”
其实,这样的严格是当时西南联大普遍要求的。“学校对学生的学习成绩要求很严,一学年选修学分的1/3不及格就留级,1/2不及格必须退学,从不含糊。”胡邦定清晰记得,当时个别学生对校长梅贻琦严格执行考核制度颇有微词,曾有人在教室的墙外侧用粉笔写上“打倒梅特涅”几个字。这个学生是用1948年维也纳三月革命时,工人、大学生反对奥地利专制独裁首相梅特涅的名号来影射梅贻琦。
但据胡邦定回忆,梅贻琦丝毫不为所动。在一次全体学生参加的“国民月会”上,梅贻琦重申了学习纪律,并且说,国家在抗战时期办学,很不容易,学生如不勤奋向学,应当于心有愧。然后,他气愤地说:“说我们是梅特涅,我们就是梅特涅!但考核标准绝不降低!”
不仅对学生严格要求,教师对自己的要求也从不含糊,哪怕是成名已久的大家。比如被尊称为“教授的教授”的陈寅恪,每每讲课,总是侃侃而谈,引经据典,更难得的是他从不拾人牙慧,“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陈寅恪先生上课,只讲新发现、新见解、新成就,这给了我们极大的震撼,做学问原来是应该这样做的。”胡邦定动情地说,4年大学生活,教师们通过启发和示范,开阔了他们的眼界和思路,教会了他们做人和做学问。
大师风范
在当时的西南联大,不论是在国内成长起来的鸿儒,还是国外学成归来的教授,普遍保持一颗赤子之心。而在诸多教授中,其音容笑貌至今还深深印在胡邦定脑海中的,首推大一时讲授伦理学的文学院院长冯友兰。
冯友兰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多年游学国外和讲学,一般人都设想他一定是一位“国际范儿”的教授。然而当冯友兰第一次出现在学生面前时,却让他们大跌眼镜,冯友兰竟然是一副土得掉渣的老夫子形象:戴深度近视眼镜,三寸长须,着蓝布长袍、黑马褂,足登中式布鞋……
胡邦定回忆,因为西南联大没有能容全部历史系学生的大课堂,教师只能在一片松树环抱的空地上讲课。有口吃毛病的冯友兰,操着浓重的河南口音,开场就说:“当年孔、孔、孔子杏坛讲学,我们今天在、在这松林里授课……”
教经济学的法商学院院长陈岱孙,也以“戴两块表”给了胡邦定不一样的感受。陈岱孙是在美国哈佛大学拿金钥匙的博士,每次上课,他都着整齐的西服,打领带,手提一个大皮包。上课时间是上午10时至12时,陈岱孙总是提前三五分钟就在教室门前散步,差一分钟左右就站上讲坛,然后准时开讲。
由于选修陈岱孙经济学的人多,只能在距生活区较远的一个能容纳200人左右的大房子里上课。起初,每当快到下课的时候,有些学生惦记着赶到食堂吃饭,不免有些躁动。陈岱孙就说:“我戴着两块表,绝不会误了你们吃饭的时间。”这种“安民告示”很有针对性,因为西南联大学生食堂一般只管午、晚两顿饭,许多学生是空着肚子来听课的。
往事如烟,胡邦定在回忆恩师们的趣事时,更多的是感念恩师们的培养,比如陈岱孙为他打下了牢固的西方经济学基础,“陈先生讲课,最大的特点是清晰、洗练,没有多余的话,字字句句都让你听得真切。像剥竹笋一样层层剖析经济学原理,从概念到理论体系都给你一个完整而明确的认识”。
人格魅力
胡邦定进入二年级以后,专业课逐步增加,而西南联大历史系的名家甚多,可谓人才济济,比如陈寅恪、钱穆、雷海宗、郑天挺、向达、张荫麟……这些名家中,胡邦定对系主任雷海宗的印象尤为深刻。
“对于雷先生,大家都说他是声音如雷,学问如海,自成一宗。他上课从不带片纸只字,每次讲述许多历史纪年,绝对准确无误。”相对于治学和教学的严谨,胡邦定感受更多的是雷海宗为人师表的力量。
雷海宗生性耿直,不因意识形态的分歧而不顾客观事实。1946年2月25日,西南联大在新校舍图书馆前大草坪为抗议苏军在东北拆机器、强奸妇女等罪恶行径举行演讲会,雷海宗讲得声泪俱下,列举种种事实谴责苏军暴行。在当时,一些拥苏的“左”派学生,包括胡邦定在内,对雷海宗的言行深为不满。
如今,近70年过去了,雷海宗穿越历史的坚持正义的呐喊,在胡邦定的眼里,也变成了深深的崇敬。“现在冷静地想一想,雷先生的义愤是很自然的,作为爱国的、维护正义的中国人,怎么能对苏军暴行钳口无言呢?从这一点可见,雷先生坚持是非的原则精神是很可贵的。”胡邦定激动地说,中国有“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的传统,作为一个中国人,特别是历史学家,焉能不顾事实,违心地沉默呢?就这点来讲,雷先生永远都是我们的师表。
铮铮风骨
1942年,胡邦定进入西南联大学习时,刚好20岁,当时饭尽管可以管饱,但没油水,每天饱尝“饥肠辘辘”之感。这也还好,学生毕竟“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教师们就没有那么好的境遇了,“老师比学生苦”是当时的真实写照,尤其是那些拖家带口的教授。
抗战时期,教授们和大后方广大教职工一样,深受通货膨胀之苦。据统计,抗战前教授的平均工资约为350元法币,同350银元等值。到了1943年下半年,物价上涨了405倍,教授们这时的平均收入为3697元法币,只相当于1937年的8.3元了。以这点微薄的工资实难养家糊口,但教授们坚持含辛茹苦,一边教书,一边科研,许多人把自己心爱的藏书卖掉以补贴生活。
比如闻一多,为了养活一家老小8口人,他还在昆明的昆华中学兼一个全职的教员,但收入仍不够开销,还要靠刻图章来维持生计。再比如吴晗,有一次,胡邦定在早市上看见吴晗提着菜篮子四处转悠,他原以为吴晗是在精挑细选好菜,走近才得知,原来他是在满市场找便宜菜。
“西南联大的教授们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他们本可以生活得不那么艰苦,可以做官,也可以接受政府的特殊津贴,但他们坚守了知识分子应有的风骨。”胡邦定回忆说,教育部有一次要给所有担负行政职务的教授特殊津贴,但25位兼院长、系主任的名教授为了与全体教师同甘共苦,毅然拒绝,这让学生们深受感动。
“这是何等胸襟,何等风骨,怎能不令人敬佩!”抚今追昔,胡邦定一脸崇敬地说,王勃在《滕王阁序》的名言: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用在西南联大教授身上最贴切不过。